28年前的整个8月,我是在一种忐忑不安的心绪中度过的。
高考已毕,尘埃落定,志愿也稀里糊涂地填过了。听大哥说学经济好,吃香,就狂选有“经济”二字的院系专业,重点非重点,一口气整了14个。远到北京,近至成都,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商业经济、政治经济,一水的经济,满纸的经济,梦话都在吼经济。
其实当年的我,对经济的内涵完全懵懂无知。生在偏远的县城,又逢物质匮乏的计划经济年代,孤陋寡闻,印象中和经济相关的是一种劣质香烟,就叫经济烟,九分钱一包。
高考和志愿决定命运,老师说事关今生穿皮鞋还是草鞋,不得已写了那么多的经济,眼前生动的,倒只有名号经济的烟卷,心里悄悄向往的,还是朝阳桥、牡丹,而中华,太高不可攀了,索性不去想。
该做的都做了。余下就是两个字:等待。
8月的故乡,和过去一样,中午燥热,早晚凉爽,东灵山多雾,大渡河汹涌。终于可以不做假期作业,不写作文,不解方程。处于暂停状态的我,第一次有了边缘人的轻松,也有了边缘人的闲愁。
徜徉在熟稔的山水田间,心中淡淡的,就有了些惜别的情愫。朦胧又有些清晰地知道,中学时代怕是无可挽留地要永远结束了,在家里的日子也是不会太长了,年 龄不大,竟少年老成地生出些明年今日我在何方的迷茫,还有惆怅,当然更多的,还是对未来生活的新奇、向往,当然也有万一落榜的恐慌。
然后,8月末的一个下午,完全没有预兆的,一个牛皮纸信封平静地送到了我的手中。录取我的学校在北方,很远。报到的时间很近,3天以后就得上路。
赶到小县城仅有的裁缝铺做衣服,我们的匆忙把老裁缝也弄得紧张起来。草绿色涤卡上装、米黄的确良长裤、老羊皮大衣,铺盖,枕头,粮食关系,副食关系,全 国粮票,户口,车票……忙忙乱乱的3天,一个个机关单位奔走,谈不上欢快,也没时间烦躁,我只是有些麻木地跟着大人们,机械地办理各种手续。
最后一个晚上,我是在闹钟的滴答声中,辗转到黎明的。
母亲没有送我多远,她只是站在从小伴我长大的老枇杷树下,一遍遍地叮嘱着渐行渐远的我。走出好远,在黎明微弱的光线里,已经看不见母亲的身影,但还能听到她的声音。
我一遍遍地应着,有些哽咽。
从我家到县城的车站有很长一段依山傍水的路,父亲陪着我,父子俩沉默地走着。
车轮转动,1980年的故乡沉默地留在我身后,我只来得及对着车窗外的父亲挥了挥手。从此关于我少年时代的所有记忆,那些山水树木,夜半雨后孤单的萤火虫,直立河中央的巨大礁石,冻红的双手,那些和一个贫寒的少年人有关的所有故事,都被我的故乡永久地悄悄收藏着了。
就这样由汽车而火车,黑白颠倒地摇晃了几天几夜。
斜挎一个黄色的帆布书包,穿一双簇新扎眼的草绿色胶鞋,小小的我有些神情恍惚地随着人流走出车站。
我的入学通知书上,除了录取的院系和专业的名称,还有到北京后的乘车路线,其中的一句话让我一直很迷糊:到北京火车站后,转乘103路快车和332路慢车到魏公村站下车。我就琢磨,这大学可够远的,坐几天火车到了北京,还得换两次火车,并且学校大约是在一个村子里。
生长在偏僻小县城的我全然不知大城市的公交汽车也是要分快慢车的,至于魏公村,也不是一个村子,而是个挺大的镇。
好在走出北京站大门,我一眼就认准了夜色中一面红色大旗,上面是龙飞凤舞的金色的大字,书写着亲切的校名。旗下有笑意盈盈的脸,后面停着漂亮的校车。我努力摆脱迷幻的感觉,踉跄着走上前去,这一来,103和332都不必担心了。
校车飞快驶过宽宽的长安街,驶过天安门,我清楚地记得长安街和天安门在路灯的照射下,呈现出一种暖暖的橘黄色,行人和车辆都不多,整个气氛是静谧的。
我在学校里安顿下来了,但也渐渐感到一种陌生和孤独。天南海北来的同学,操着蹩脚的普通话,和中学里最不一样的是再没谁管你,全靠自理。水土不服,鼻孔 流血,饮食也不习惯,除了馒头还是馒头,一个月才8斤大米。数学老师在课堂上用一连串清脆卷舌的北京话大讲微积分,而在高中我是学文科的,每天在教室里坐 飞机的感觉真让人沮丧。我甚至想要能转学回四川就好了,离家近,中学同学多。还有白米饭和回锅肉。
就因为想家和孤独,女生宿舍里上演过一个人哭了,其他人劝,结果连锁反应,一个房间接一个房间,而后一层楼、一幢楼,哭成一团的故事。还好,我总算没有哭,但也仅仅是强忍着,若有个风吹草动,肯定就翻江倒海,泪如雨下了。
这种境况的改变是在10月的一个中午。
那天下课回来,情绪低落的我收到了好几封来信,有两封是中学女同学的,其中一位在信中写道:“听说香山的红叶很美,能否寄回几片……”
正是这几封来信使我猛然醒悟:我这是在上大学呢!胸前白色的校徽和大街上那些羡慕的目光都在提醒我,大学生的自豪感一下子充满了我16岁的心。接下来,我走出了初入大学的迷茫,真正融入了我的大学。
后来,在回家的日子里,我去了那个女同学的家。
我很惊异,昔日黄毛丫头如今已亭亭玉立,我们的相处是拘谨的,谈了些什么全忘了。只记得告辞出来后,同去的朋友说:“你注意到了吗,她的床头上大大地写着几个数字,100081。”
那是我学校的邮政编码。
斗转星移,人生若梦,二十多年的岁月就这样不露声色地流逝了,我的儿子也到了该读大学的年龄。
父母都不在了,当年那个和我一起彻夜不眠的闹钟已经老得不能再走动,但我至今仍然保留着。总感觉它是个有灵性的物件,尤其它曾精确地记录了我离开故乡的时间,也诚实地见证了我16岁以前所有的日子里,那些过早的辛酸和单纯的快乐。
我总在猜想,倘若有朝一日,我修好它,就在它的时针分针重新沙沙走动起来的时候,是否会电闪雷鸣,大雨滂沱,或者万籁俱寂,月白风清,那该是昔日重来的 序曲啊!那些逝去的亲朋,那些凋萎的花朵,那些枯死的树木,还有专属于1980年的所有浪花和云朵,它们必定在那一刻重新振作并鲜活起来,与我叙旧、握 手,同我流泪、唱歌,而我最终必定会被一声声熟悉又亲切的召唤所吸引,我会形单影只地循着声音,走向那幽暗又温暖的远处,那是我1980年的母亲啊!她站 在故乡的那棵树下,正在送别她最小的儿子离家,初秋黎明的寒气里,她有着模糊而苍老的面容。(文/格桑亚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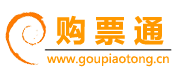




 京公安网备11011202001818号
京公安网备11011202001818号